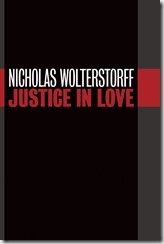在柴玲的第一封与第二封公开信中,她所提出的主题是“饶恕”,然而对她的批评者们提出的主题是“公义”。有意思的是,公开赞同柴玲的人大多匿名(例如基督日报采访的这位“爱德华牧师”),而公开批评柴玲的人大多实名。支持的躲躲藏藏,批评的理直气壮,为什么呢?
首先,“饶恕”是否符合圣经和基督徒伦理?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圣经有多处经文鼓励基督徒放下仇恨和饶恕,甚至爱自己的仇敌。在教导主祷文之后,耶稣就教训他的门徒说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,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”表明饶恕不单单是基督徒应有的美德,也是基督的命令。保罗在新约书信里继续这一教导,“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,总要彼此包容,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,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”
其次,“饶恕”一定要对方道歉在先吗?如果对方犯了错,没有道歉、没有认罪,我是不是就应该一直不饶恕?柴玲在第一封公开信中引用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“父啊,赦免他们,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。”来支持“无条件的原谅”。这也是对柴玲观点的诟病之一:中共没有道歉、没有认罪、没有平反,何谈“饶恕”?我想在这里需要认识“饶恕”的两个层面:(1)放下心中的苦毒与仇恨;(2)与伤害者和解。柴玲所说她的“饶恕”,我更愿意理解成是第一个层面,即她愿意放下心中对杀人者的苦毒和仇恨,不让仇恨继续捆绑她。这种“放下”,的确不需要对方的认罪,因为她要解决的是自己内心的问题,避免让仇恨、报复、“以命抵命”、“以暴易暴”成为心中的偶像。但是第二个层次的“饶恕”,即“和解”则需要双方的努力,需要对方的道歉和悔罪,这也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里所说的饶恕:“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,又七次回转,说,‘我懊悔了’,你总要饶恕他。”我放下苦毒、不被仇恨捆绑是无条件的,但是双方和解(Reconciliation)是有条件的。
第三,柴玲和我上面引用的经文中所说到的“饶恕”都是讲到基督徒的个人生活中需要饶恕,甚至保罗讲到基督徒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,应当的反应是“不要自己伸冤,宁可让步,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,主说,伸冤在我。我必报应。”但是在讲到公共社会的议题时,圣经所主张的是“公义”。没有人能够代替别人去饶恕,当一个不公义事件导致多人受冤屈,或是像奥斯威辛、夹边沟、集中营、六四这类惨绝人寰的群体性悲剧面前,没有人能够代替别人“饶恕”或是要求别人“饶恕”。因为公义首先需要得到申张。如果说在基督徒的个人生活面对不公时,“饶恕”比“公义”优先,那么在公共生活中“公义”应当比“饶恕”优先。
Wolterstorff 在Justice In Love一书中也同样论述这个问题。他认为“爱”与“正义”之间的张力在耶稣的时代完全就是一个伪命题。他说,“在登山宝训耶稣的教导中我们可以看到,用公义对待邻舍就是爱邻舍的方法之一。爱不是放弃公义的善行。”他进一步延伸认为放弃公义的饶恕是“不经意的错误理解了饶恕的意义”(inadvertently mischaracterised the very moral structure of his own action,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理解)。一个人不能够饶恕一个仍然留在罪行中的杀人犯(one cannot forgive a murderer who still "stands behind the deed." p.173)。然而,他也同意放弃个人的复仇,将一切交托给神,的确是基督的教导。
当我去年读到柴玲的第一封公开信时,我赞赏她的勇气说出她的决定,我也理解为她所说的“饶恕”是第一个层次:放下心中的苦毒与仇恨,不以复仇为偶像。但是问题在于,这需要发表“公开信”吗?是不是她希望这一独特的声音、这一“反文化”(中国文化特别崇尚复仇,想想《赵氏孤儿》和武侠小说吧)的举动带来福音的果效?我的理解可能过于善意了。她今年的第二封公开信进一步劝告六四难属(丁子霖)也要“饶恕”,看来她字典中的“饶恕”是指第二层次的“饶恕”,而且是公共社会中的“饶恕”,我想,这就过头了。
尽管我认为(如果两者对立的话)在公共生活中“公义”的优先高过“饶恕”,但是正如Wolterstorff所指出的,公义本身与爱或许并不矛盾,只是我们将其对立起来了。在一片“公义”怒吼中,我们也需要“饶恕”的声音,所以柴玲做出了她的贡献,也带来了思考,从这一点来说,她的公开信是有价值的——尽管你我不一定同意或接受她的观点和诠释。基督徒在公共议题上,一个单独的个体很难做到所谓的“客观公正”、“合乎中道”,因为任何社会政治解读都必然带着自己的经历和文化,所以神将有着不同侧重、乃至不同“极端”的基督徒放在这个“光谱”中,也算是一种“中和”。